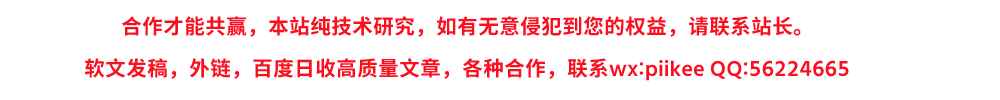耿姓取名還有2021年耿姓起名
本篇文章給大家談談耿姓取名,以及2021年耿姓起名的知識點,希望對各位有所幫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文章詳情介紹:
國學經典中千載難逢的馮氏佳名,個個好聽又小眾,從此取名不發愁
馮姓取名,馮姓比之朝代姓氏,更加單純,更加純粹。現代漢語當中的注解,非常簡單,一個字,姓。而馮姓取名,應當在自嗨與共鳴之間,尋求一個微妙的平衡。更大的意義上,應當照顧名字的社交性質。
【城名】出自聶夷中《早發鄴北經古城》:但耕古城地,不知古城名。
城:指圍繞都市的高墻和都市。用作人名意指堅毅、堅不可摧、百折不摧之義; 名:指人或事物的稱謂。聲譽,有聲譽的,大家都知道的。用作人名意指名聲、聲譽、功業之義。
【圣文】出自胡元范《奉和太子納妃太平公主出降三首》:圣文飛圣筆,天樂奏鈞天。
圣:指通達事理、聰明、神圣的、神通。用作人名意指才華、機智、氣度、有本領之義; 文:指記錄語言的符號,如文字;人類勞動人果的總結,如文化,文物;文華辭采、溫和,如文質彬彬,文靜,文雅。用作人名意指文采、聰明、文靜內斂。
【耿月】出自王惲《眼兒媚》:滿簾夜月耿霜秋。
耿:明亮,光明的意思;正直、剛直,如忠心耿耿。用作人名意指剛正不阿、耿直、積極、前途光明之義。月:指月亮,月亮的傳說也多與女性有關,因此月字又常被用作女性取名。常見詞語月色、月光、月明。用作人名意指貞潔、潔凈、智慧、愛與美的象征之義。
【秋勝】出自曹勛《臨江仙》:連夜陰云開曉景,中秋勝事偏饒。
秋:秋字的本義是一年的第三季,指莊稼成熟收獲的時期。用作人名意指成熟穩重、收獲、成功之義; 勝::一般指勝利、戰勝,如克敵制勝;也指有能力擔當,如勝任愉快。用作人名意指有謀略、有才能、聰明之義。
【睿哲】出自李賀《其二》:皇漢十二帝,唯帝稱睿哲。
睿:意為明智,深遠,通達。可起名如睿遠、睿穎、碩睿、超睿。用作人名意指睿智、精明、光明之義 哲:本義為聰明,有智慧。也指聰明、有才能的人。用作人名意指冰雪聰明、才智卓越、有學識之義。
【昌鴻】出自胡曾《詠史詩·武昌》:王浚戈鋋發上流,武昌鴻業土崩秋。
昌:本義是善,正當,指正當的言論。還有興盛繁榮之義。用作人名意指善良正直、興旺繁盛之義; 鴻:大雁;書信;旺盛,興盛;學識淵博。用作人名意指學富五車、興盛、文采斐然之義。
【明哲】出自杜甫《北征》: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
明:指亮,清楚,懂得,如明白,明亮;指睿智,如英明,賢明。用作人名意指明理、明智、睿智。 哲:本義為聰明,有智慧。也指聰明、有才能的人。用作人名意指冰雪聰明、才智卓越、有學識之義。
【君民】出自陽枋《念奴嬌》:君民堯舜,老翁揩眼勛業。
君:本義:君主,封建時代指帝王。指主宰、統治,貴族,尊貴,道德品行高尚的人。如君子。用作人名意指皇室風范、尊貴、正直。 民:指人或人群;也指民眾的希望,心愿,治理,財富。用作人名意指安定、勤奮、純正之義。
蒙元時期云南蒙古語地名“哈剌章”“察罕章”釋義
江西地名研究
關注我們,獲取更多地名資訊
關注
摘要:哈剌章、察罕章是元代蒙古人對云南境內大理、麗江地區的稱呼,但其確切含義,至今仍存爭議。以往學者大多根據《經世大典》和《元史·兀良合臺傳》中的記載,分別將之解釋為烏蠻和白蠻,但該觀點存在諸多問題,難成定論。本文認為,14世紀初期伊利汗國宰相拉施特編撰的《史集》將哈剌章譯為“大國”或“大的地區”是迄今為止最為合理的解釋。察罕章的含義很有可能與江水、雪山等具有白色意象的自然地理事物有關。哈剌章與察罕章含義的背后,呈現出蒙元時期云南地區漢、梵、蒙、藏多種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的格局。
關鍵詞:哈剌章;察罕章;《史集》;云南
蒙元時期,“哈剌章”“察罕章”分別被用于指稱云南境內的大理和麗江地區,但二者的確切含義,至今仍存爭議。此前學界大多依據《經世大典敘錄·征伐》和《元史·兀良合臺傳》中的記載,將哈剌章、察罕章分別解釋為烏蠻和白蠻。早在1904年,法國學者伯希和(Paul Pelliot)在《交廣印度兩道考》中,認為哈剌章和察罕章應進一步譯為“黑爨”和“白爨”,并指出由于南詔王室長期與烏蠻部落通婚,且南詔國政治中心位于大理,受此影響,蒙古人征服云南后,便將南詔視為烏蠻,進而稱大理為哈剌章,但對察罕章與白爨的關系,伯希和并未詳論。此后,伯希和的觀點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影響,法國學者沙畹(Edouard Chavannes)在《麗江地區的歷史和地理文獻》一文中,便采納了伯希和將察罕章譯為白爨的觀點,馮承鈞亦將其收錄進漢譯本《馬可波羅行記》注釋中。然而不久之后,伯希和的“黑爨、白爨說”逐漸受到中國學者的質疑。1980年代,方國瑜在《中國西南歷史地理考釋》一書中這樣說道:
“譯名當有所本,不聞大理國時麗江、大理居民稱稱戎、稱蚺、稱爨之說,何得有此譯名,白爨、黑爨,即西爨白蠻與東爨烏蠻,其地在滇東及滇東北,與麗江、大理混為一談,不通之論也······惟有不可解者,元代記錄稱麗江為察罕章,大理為哈剌章,當時麗江以納西族為主,‘納’有黑意,白人取白意,則察罕應稱大理,哈剌應稱麗江,而記錄適得其反,何以如此,則不得而知也”。
方國瑜認為,南詔、大理國及元代,大理地區的主體族群是白蠻而非烏蠻,麗江地區則為烏蠻類中的磨些蠻,即今日納西族的主體,而“納西”意為“黑人”,也與“白”無關,因此將哈剌章、察罕章分別解釋為烏蠻和白蠻的記載未必準確。同時,方國瑜根據云南歷史上爨地的分布范圍,反對伯希和將哈剌章、察罕章與黑爨、白爨相聯系的觀點。方國瑜對伯希和觀點的批判,將該問題的研究提升到了更高的層面,即不能僅滿足于審音勘同,還需結合歷史文獻,考察有關名詞的含義及使用范圍能否等同。但遺憾的是,方國瑜并未就哈剌章、察罕章含義做進一步探討。近年來,學界對該問題的研究亦有所推進,開始有學者注意到“察罕”“哈剌”二詞在蒙古語中表示的深層次意象。然而到目前為止,前人的研究基本上是在首先接受“哈剌章即烏蠻,察罕章即白蠻”這一前提下進行的,少有學者懷疑過該解釋的準確性,因而得出的結論自然存在矛盾之處。同時,這也讓人們極易對烏蠻、白蠻等族群概念以及蒙元時期云南境內族群的實際分布狀況產生混淆。因此,厘清哈剌章、察罕章二詞的確切含義,對準確理解元代云南地區的族群關系顯得極為重要。值得注意的是,14世紀初期伊利汗國宰相拉施特編撰的《史集》中多次出現有關哈剌章的記載,并提供了一種不同于《經世大典》和《元史》的解釋,但迄今為止并未得到學術界的足夠重視。有鑒于此,筆者擬結合前人已有研究,通過爬梳史料,明確哈剌章、察罕章在蒙元時期的具體指代范圍,以及唐、元時期云南烏、白蠻的劃分標準和分布情況,分析《史集》對哈剌章含義記載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并根據元代麗江蒙古語地名的命名特點,對察罕章一詞做出更為合理的解釋。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揭示出哈剌章、察罕章含義背后蘊藏的文化史信息。
一、“哈剌章”指代的地域范圍
目前學界一般認為,在蒙元時期,哈剌章有狹、廣二義,狹義指云南境內的大理地區,廣義則指整個云南行省。這一說法基本準確,但略顯籠統。若涉及對哈剌章含義的準確定位,就不得不首先明確哈剌章在云南最早出現并使用的時間及其指代的各類范圍不等的區域。
據《大元混一方輿勝覽》卷中《云南等處行中書省·大理路·沿革》記載,大理城“古名葉榆,南詔之都會也,蒙氏為陽瞼,謂之羊苴咩城。段氏有國,號大理,歸附后,謂之哈喇章,至元間立總管府”。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引文雖系于大理路沿革條之下,但從具體語境看,并非是在敘述大理路的沿革,而是在交代大理城的始末。因為其中提到的地名,雖可泛指大理城周邊地區,但在引文中均側重在特定的城市上,如葉榆乃南詔都會,陽瞼即羊苴咩城。由此不難看出,引文中的哈剌章,主要強調的對象應當是大理城。不過,由于大理國國號與皇都大理城的名稱完全一致,因而這里的“哈喇章”也可表示大理國。這條材料反映出用哈剌章指代大理的做法是在元憲宗三年(1253)大理歸附蒙古至大理設路總管府這一期間出現的。根據相關研究,《大元混一方輿勝覽》出自元代類書《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于大德十一年(1307)刊刻。與眾多記錄元代云南行省地理沿革的史料相比,該書成書年代較早,且參考了《元一統志》中有關云南的部分,該部分主要依據李京大德七年報送元廷的《云南志略》而寫成。故綜合來看,該書對哈剌章的記錄應當是比較可信的。
除漢文史料外,《馬可波羅行紀》中亦有關于哈剌章的記載。其中第119節(漢譯本第122章)提道:“從前述之鴨赤城首途后,西向騎行十日,至一大城,亦在哈剌章州中,其城即名哈剌章”。鴨赤城即當時云南行省的治所所在地中慶城,大理城在中慶以西,因此馬可波羅筆下名為哈剌章的城市,無疑是大理城。這一記載進一步明確了哈剌章指代的最小地域范圍是大理城。在《馬可波羅行紀》中,哈剌章除了指大理城外,還表示大理國曾經直接統治的地區。馬可波羅描述的哈剌章地區,主要包括了以大理、中慶為中心的洱海盆地和滇池盆地,這一區域與大理城、大理路相比,范圍明顯擴大。此前學界多把第118~119節中描述的哈剌章州視為云南行省,但若細讀該部分,則不難發現,這里的哈剌章包含的范圍與大理國末期控制的疆域基本相同,但遠小于云南行省。首先,馬可波羅在述及哈剌章范圍時,將之限定于金沙江以南,強調過了金沙江才進入哈剌章,而隸屬云南行省的建昌地區 (羅羅斯宣慰司)并未包括在內。此外,在述及金齒地區(今云南德宏、臨滄一帶)時,從《馬可波羅行紀》的表述方式看,金齒與哈剌章是并列而非包含關系。金齒早在中統初年就歸附蒙古政權并隸屬云南。若這里的哈剌章指云南行省,按理說不應將二者并列。大理國疆域,前期和后期存在不同。據《元史·地理志四》對云南各地在大理國時期隸屬情況的記載可知,蒙古入侵前夜,大理國直接控制的地區,東抵曲靖,西達永昌(今云南保山),南至臨安(今云南建水)、通海一帶,北至金沙江。烏蒙(今云南昭通)、金齒、廣南(今云南文山)、建昌(今四川涼山)等之后被云南行省統轄的地區當時均不在大理國直接統治的范圍內。因此,該處的哈剌章應理解為大理國后期統治的區域。
拉施特在《史集》中也多次強調哈剌章是蒙古人對大理國的稱呼。例如在《史集·中國史》的開篇部分,就提到“在乞臺的西南方還有一個地區,名叫大理,蒙古人稱之為哈剌章”。此外,哈剌章在元代也被用于稱呼云南行省。自至元十一年云南行省設立后,哈剌章在漢文史料中的使用頻率逐漸減少,但在元代中后期的一些非漢文史料中,仍用哈剌章稱呼云南。吐魯番出土的U4707號元代回鶻文文書記錄了元文宗時期云南行省右丞月魯帖木兒率軍前往云南平定禿堅、伯忽之亂的史事,其中便將云南稱為“哈剌章”。
綜上可知,根據《元混一方輿勝覽》《馬可波羅行記》《史集》三種成書年代在13世紀末至14世紀初的不同語種的史料,可以明確哈剌章一詞所指的區域,由小到大依次是:大理城、大理國、云南行省。哈剌章指代的地域與“大理”密切相關,因此對哈剌章含義的討論也應當限定在“大理”這一范圍內。
二、唐、元時期的“烏蠻”與“白蠻”
《經世大典敘錄·征伐》和《元史·兀良合臺傳》將哈剌章解釋為烏蠻,而哈剌章在蒙元時期主要指大理地區,那么大理與烏蠻究竟有無關系?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要考慮當時大理地區的族群狀況及烏、白蠻在古代云南歷史上的具體含義和分布范圍。
烏蠻與白蠻最早在唐代被用于稱呼云南地區的各類族群,有關記載最早集中出現在唐人樊綽撰寫的《蠻書》中。樊綽是安南經略使蔡襲的幕僚,于咸通三年(862)來到安南。當時正值南詔大舉進攻安南的嚴峻時期,出于對南詔問題的關注,樊綽利用手頭已有資料和自己調查所得,寫成了這部記載南詔歷史地理及風土人情的《蠻書》。關于云南的烏、白蠻,自20世紀以來,已有眾多學者進行過研究,其中方國瑜對該問題的研究是迄今為止最全面的。方國瑜指出,根據樊綽《蠻書》記載,烏蠻、白蠻是唐代中原內地漢人對西南地區土著族群的泛稱,是“他稱”而非當地土著人群的“自稱”。烏蠻和白蠻并非指某個具體族類,其區分標準是各族群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與內地漢人的接近度,接近于漢人的稱為白蠻,與漢人差別較大的稱為烏蠻,類似于漢文史書中常見的“熟蠻”和“生蠻”這組概念。《蠻書》對烏、白蠻文化特征有不少詳細的描述,例如烏蠻所居“多散林谷”;白蠻死后“依漢法為墓,稍富,室廣栽杉松”,烏蠻則“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燼,掩以土壤,唯收兩耳”等。可見,文化是劃分烏、白蠻的主要標準。受云貴高原自然地理環境的影響,烏蠻、白蠻在云南各地呈現垂直化分布特征。具體而言,烏蠻主要居住在山區,白蠻則大多生活在壩區。
大理地區族群狀況最早且最詳細的記錄,是唐朝貞觀二十三年(649)右武侯將軍梁建方征討云南洱海地區時寫下的《西洱河風土記》,后被收錄到唐人杜佑編撰的《通典》中。據《通典·松外諸蠻》條記載:
“其西洱河,從離州西千五百里,其地有數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戶,無大君長。有數十姓,以楊、李、趙、董為名家。各據山川,不相役屬。自云其先本漢人。有城郭村邑,弓矢矛鋌。言語雖小訛舛,大略與中夏同,有文字,頗解陰陽歷數。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莊之余種也。”
西洱河即今日之大理洱海。唐代初期,這里還處于部落林立的狀態。當地人具有“楊、李、趙、董”這類漢姓,大多認為自己的祖先是漢人,風俗文化亦與漢人相近,且洱海周邊的地形皆以平壩為主。因此,按唐代的族群分類標準,居住在洱海盆地的居民主要為白蠻。
公元8世紀起,在唐朝的扶植下,南詔逐漸壯大并統一洱海地區。隨后向東擴展,兼并云南東部的爨氏領地,在西南地區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區域性政權。南詔國的都城一直位于大理,因而南詔王室的族屬也成為學者們討論哈剌章與烏蠻關系的重要依據。關于南詔王室族屬問題,至今仍有爭論。有部分學者認為南詔統治者為烏蠻,其依據是南詔多位國王長期與烏蠻部落通婚,這也是伯希和論證哈剌章為黑爨的主要根據。然而,在南詔時期,洱海盆地的白蠻大族在南詔政權中占有重要地位,不僅擔任絕大多數重要官職,還在數次對外戰爭中擔任軍隊統帥,這在《南詔德化碑》中有詳細記載。此外,《蠻書》所記南詔各類風俗中,多半與漢地相近。如“衣服略與漢同”,“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山棟下宇,悉與漢同”等。因此,從文化角度看,南詔政權占統治地位的人群以白蠻為主,有著與中原漢地相似的文化特征。南詔王室與烏蠻聯姻僅是出于進一步控制云南東部烏蠻地面這一政治層面的考量,并未對洱海地區的族群構成產生顯著影響。在敦煌藏文文書中,亦見吐蕃用烏蠻(mywa-nag-po)、白蠻(mywa-dkar-po)區分南詔統治下的兩類族群,該分類方式應當是從唐朝傳入的,因為在南詔時期遺留下的碑刻等各類文獻中,并無南詔當地人將自身稱為烏、白蠻的記載。趙心愚通過對P.T.1287號(贊普傳記)文書的分析,認為該文書中的白蠻(mywa-dkar-po),應指南詔王統治下的南詔本部。可見,唐代吐蕃人亦未將南詔視為烏蠻。繼南詔之后建立的大理國,其統治族群為白蠻,已是學界共識,大理地區白蠻占主導地位的趨勢貫穿了整個大理國統治時期。蒙古人與大理國的接觸始于13世紀中期,此時距大理國建國已有三個多世紀,因此蒙古人對云南族群的認識應直接來源于大理國而非此前的南詔,用南詔王室的族屬來論證蒙元時期烏蠻與大理的關系顯然并不合適。
蒙元時期,關于云南烏、白蠻最早的記載為劉秉忠《藏春詩集》中數首題為《西番道中》《烏蠻道中》《烏蠻》《過白蠻》《南詔》《下南詔》《滅高國主》的詩文。在1253年蒙古征討大理國的軍事行動中,劉秉忠一直陪伴忽必烈左右。從排列順序上看,這幾首詩與忽必烈親自統率的中路軍進軍路線相同。詩中烏蠻、白蠻的具體地點雖無法考證,但從詩文的排序和描繪的環境來看,《烏蠻道中》《烏蠻》二詩所處位置應是金沙江以北的青藏高原東部山區,這一地區為吐蕃之地,在元代由宣政院管轄,并不屬大理國和云南行省。《過白蠻》則位于金沙江以南的平壩區。顯然,在當時人看來,烏蠻的分布并不限于云南,生活在云南周邊山區的族群均可被稱為烏蠻,白蠻則主要指居住在壩區的族群,這與《蠻書》中的族群劃分原則基本一致。同時,上述詩文也反映出,像劉秉忠這類跟隨忽必烈親歷云南的北方漢人亦未將大理國、大理城以及當地的白人視為烏蠻。用南詔稱呼大理國是詩文創作中常見的托古手法,并不能證明蒙古統治者因不知大理國國號而沿用南詔舊名。蒙古征服云南后,對當地族群的劃分總體上延續了前朝的方式,但仍有部分調整。在蒙古征服云南早期,“烏蠻”“白蠻”仍是區分云南土著人群的常用二分法。然而隨著元朝統治者對云南統治的不斷深入,對當地族群的認識也更為具體。由于白蠻的文化特征與漢人極為接近,因此“白蠻”一詞逐漸被“白人、焚人”取代,“烏蠻”雖仍被保留,但使用頻率逐漸下降,主要指居住在山區的羅羅人。元人李京《云南志略·諸夷風俗》對元代云南各族群的分布地域有明確記載:
“白人,有姓氏······中慶、威楚、大理、永昌皆人,今轉為白人矣”。
“羅羅,即烏蠻也······自順元、曲靖、烏蒙、烏撒、越,皆此類也”。
李京自大德五年(1301)至大德七年間擔任云南烏蒙烏撒宣慰副使,曾親歷云南多地,對云南族群分布的記載應當是準確可信的。由此可見,元代大理地區,白人為最主要族群。烏蠻(羅羅)主要分布在云南北部、東部和東北部山區,與大理無直接關系。哈剌章指代的大理地區,與烏蠻無關。同時也可看出,元人亦未將白人稱為烏蠻。因此,將哈剌章或白人視為烏蠻的觀點,與元代云南地區的族群分布情況明顯不符。一般認為,蒙古人缺乏華夷觀念,通常不會將被征服地區的人群視為“蠻夷”。因此,蒙古征服者不太可能在蒙古語這套自身已有的話語體系中用烏蠻稱呼白人和大理國。即便蒙古人知曉了烏蠻一詞,那也一定是通過身邊的漢人了解到的,也就必然會繼承漢人對烏蠻的界定標準,而不太可能根據以黑為貴的本族傳統,將大理白人稱為烏蠻。更何況這種推理目前不但找不出史料依據,而且現有關于元代云南族群分類的相關材料,均對其構成反證。
那么如何解釋《經世大典》和《元史·兀良合臺傳》將哈剌章譯為烏蠻呢?這需要從這類記載出現的具體語境、《經世大典》和《元史·兀良合臺傳》之間的關系以及《經世大典》編撰的局限性三個方面進行分析。據《經世大典敘錄·征伐·云南》:
“憲宗三年,世祖征西南夷,由吐蕃入云南,命兀良合臺自旦當嶺入,降摩些部,涉金沙江,攻下諸砦,取龍首關,世祖遂入大理城。兀良哈臺分兵取附都善闡烏爨,次羅部府,大酋高升拒戰,大破于淺可郎山下。升嬰城自守,城際滇池,三面皆水難攻。圍七日,始克。國主段智興柔暗,權臣高祥方謀篡弒。及大兵至,智興走匿昆澤,追及善闡,獲之。世祖入其城,秋毫不犯。尋引兵入吐蕃,酋長唆火脫因塔里堅守,兀良合臺進攻,懼而出降,用為向導,襲取白蠻,譯曰察旱章,蠻依山固守,兀良合臺令其子阿術殺蠻退走。乘勝至烏蠻,曰哈剌章,攻破水城。四年春,世祖還。兀良哈臺至烏蠻之都,曰押赤城。依山阻水,不可近······”
押赤(今昆明)是大理國的第二首都,元人將押赤稱為烏蠻之都,并不意味著押赤城內居住的人群是烏蠻,而應理解為押赤是大理國控制云南東部烏蠻部落的重要據點。云南東部長期被稱為爨地,在唐朝中葉以前為漢化程度較高的爨氏家族的領地。爨地分為東爨、西爨,東爨多烏蠻,西爨多白蠻。南詔建立后,逐漸向東拓展,并最終兼并爨地。據《蠻書》記載,“閣羅鳳遣昆川城使以兵圍脅西爨,徙二十余萬戶于永昌城。烏蠻以言語不通,多散林谷,故不得徙······烏蠻種類稍稍復振,后徙居西爨故地”。爨地的主體族群自此變為烏蠻,“爨”也成為烏蠻的代名詞。為加強對滇東地區的控制,南詔曾修筑拓東城,大理國皇帝則允許高氏一族世襲善闡侯,并長期駐守該地,以加強對大理國東部烏蠻部落的控制,但隨高氏而來的大理白人僅居住在城市,未改變爨地以烏蠻居多的族群結構,善闡城之外的主體居民仍為烏蠻。如今昆明周邊的地名多為彝語詞匯(如祿勸、呈貢、塔密等),便是例證。《經世大典》將烏蠻與哈剌章相聯系時,是在敘述兀良合臺率軍進攻包括善闡在內的云南東部烏蠻聚居區(亦稱三十七部)這一背景下產生的。之所以這樣認為,是由于《經世大典》在表述時常將附都善闡和烏爨、烏蠻等同類概念連為一體。然而,在談到攻打大理城時,《經世大典》反而未將其稱做哈剌章,也未將大理及當地的白人稱為烏蠻,可見《經世大典》的編纂者并不知道哈剌章最初指代的是大理城,因而誤認為哈剌章與烏蠻是同義詞。此外,亦從未有元代文獻記載元人曾用哈剌章來單獨指代西南地區的某個烏蠻聚居區。上文引述的劉秉忠詩文將云南之外的吐蕃東部地區稱為烏蠻,而哈剌章在蒙元時期指代的地域范圍并未擴展到吐蕃境內,更何況“章”與“蠻”在語言學方面找不出任何聯系,因此烏蠻和哈剌章始終無法準確對應。或許會有學者認為,引文“乘勝至烏蠻,曰哈剌章”中的哈剌章,應指大理國。考慮到哈剌章有狹、廣二義,這樣理解也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能由此認為這里的烏蠻指的就是大理國的主體族群——白人。原因是大理國內部并非全是白人,壩區之間的山林地帶同樣生活有烏蠻部落。
筆者認為,《經世大典》的編纂者極有可能在不了解哈剌章原始含義和指代區域的前提下,僅憑“哈剌”在蒙古語中意為“黑色”這一點,便把哈剌章與烏蠻隨意比附。值得注意的是,《經世大典》中的這段文字存在諸多問題,例如將大理國皇帝段興智的名字誤作“段智興”,以及在記錄蒙古軍隊進攻大理國各地時,時間順序前后顛倒,誤將蒙古軍隊進攻善闡的時間記為元憲宗三年,并把“世祖入其城”一語系于攻破善闡后,誤認為忽必烈參與了圍攻善闡追捕段興智的戰斗。然而據《元史·世祖紀》,忽必烈在元憲宗三年十二月攻下大理后便北還,元憲宗四年五月已至六盤山,而善闡之戰發生在元憲宗四年春夏之際,因而忽必烈不可能前往善闡。且后文又說元憲宗四年忽必烈北返后,兀良合臺率軍進攻滇池附近的押赤城,顯然負責修撰《經世大典》該部分的人員并不知道善闡和押赤是同一座城,誤將同一事件分別系于不同年份。已有學者指出,《經世大典》的一線編纂者多為漢人。生活在元代中后期的漢地文人可能對哈剌章這類當時尚不太常用的非漢語詞匯以及七十多年前蒙古征伐大理國的具體經過缺乏準確認識,故誤解了哈剌章的含義和相關史料中的內容。
《元史·兀良合臺傳》的記載與《經世大典》極為相似,也是在兀良合臺進攻善闡時提到哈剌章的:
“甲寅秋,復分兵取附都善闡,轉攻合剌章水城,屠之。哈剌章,蓋烏蠻也。前次羅部府,大酋高升集諸部兵拒戰,大破之于洟可浪山下,遂進至烏蠻所都押赤城。城際滇池,三面皆水,既險且堅······至昆澤,擒其國王段興智及其渠帥馬合剌昔以獻”。
值得注意的是,成文年代早于《經世大典》且收錄于王惲《秋澗集》的《大元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兀良氏先廟碑》在記述兀良合臺隨忽必烈征討云南的相關史事時,并未稱哈剌章是烏蠻。依據實錄修成的《元史·憲宗紀》和《元史·世祖紀》中亦未見將哈剌章解釋為烏蠻的記載。因此,從現有材料來看,將哈剌章譯為烏蠻的做法應當不早于元文宗時期。通過比對《經世大典》和《元史·兀良合臺傳》關于哈剌章記載,不難看出二者在表述上的相似之處。筆者認為,《元史·兀良合臺傳》對哈剌章的解釋極有可能源于《經世大典》,《元史》編纂者因不明哈剌章之具體含義,故沿用了《經世大典》中將哈剌章譯為烏蠻的錯誤解釋。此外,《元史·兀良合臺傳》將大理國末代皇帝段興智和他的梵文名號“馬合剌昔”(Maharaja)誤認為兩人,也反映出當時漢人對這類不常用的非漢語詞匯極不熟悉。因而,研究哈剌章一詞的含義,有必要參考相關成書年代更早的非漢文文獻。
三、拉施特《史集》關于“哈剌章”的記載
在蒙元史研究領域中,14世紀初期伊利汗國宰相拉施特用波斯文編寫的《史集》(Jāmi al-tawārīkh)是一部極為重要的史料。《史集》中對哈剌章的含義有明確記載,但它提供了一種與《經世大典》《元史》等漢文文獻不同的解釋:“大國”。漢譯本《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冊《成吉思汗紀》中提到“漢人稱哈剌章為大理,意為大國。這塊領地土地遼闊,如今也歸附了合罕”。雖然成吉思汗未曾攻打大理國,但這處記載應當看做是對大理國名稱的一般性描述,與上下文時間無關。同時,這條材料也明確了哈剌章在漢語中的對應概念是大理而非烏蠻,這和上文提到的諸種文獻對哈剌章指代區域范圍的記載相吻合。《史集》第二卷《忽必烈合罕紀》中亦提到蒙哥曾派忽必烈進攻哈剌章和察罕章地區,“那兩個地區,在漢語中稱做大理,意即大國,忻都語作犍陀羅,我國則稱做罕答合兒”。據上文所述,哈剌章有狹義、廣義之分,這里的哈剌章,應是其狹義用法,指大理城及周邊地區,不包括麗江。由此不難看出,上述兩條材料在“大理”“哈剌章”與“大國”三者間搭建了一座含義上相互關聯的橋梁,即“哈剌章=大理=大國”。此外,《史集》第二卷《忽必烈合罕紀》在記載忽必烈后裔的部分中,提到忽必烈第五子“忽哥赤死后,合罕命他(也先帖木兒)承襲父位,統轄哈剌章地區。在忻都語中,該地區名為犍陀羅,意即大國”。需要注意是,在《史集》波斯文抄本中,并無標點,此處的標點符號是漢譯本譯者加入的,故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們認為“大國”是用來解釋“犍陀羅”的。如不考慮文中標點,并結合犍陀羅的含義,那么這里的“大國”應當是對哈剌章的解釋。據《史集》記載,伊利汗國與印度之間往來頻繁,將云南稱為犍陀羅的說法正是由印度商人帶到伊朗的。受此影響,伊利汗國也用“坎達哈兒”稱呼云南地區。在梵文中,犍陀羅(Gandhar)意為“香的、香遍”,與“大”無關。歷史上,犍陀羅曾是古代印度的一個佛教王國,位于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交界的白沙瓦地區。隨著印度佛教向外轉播,犍陀羅的使用范圍也超出了印度。伯希和指出,中南半島北部的印度化國家,均有在本國建立一個新印度的習慣,即把國內及周邊地區的地名梵化。南詔、大理國時期,佛教由印度傳入云南并日漸盛行,故犍陀羅一詞被移植到云南。在眾多明清史料中,大理國常被稱為妙香佛國也與此有關。對于波斯語(vilāyat-i bo-zork)一詞,美國學者薩克斯頓(W.M.Thackston)將其譯為大省(big province)。然而在波斯語中,既可指省份,也可表示國家、地區。在下文描述契丹、蠻子等地區時,拉施特均用了這個詞。蒙古征服大理國初期,并未立刻在當地設立行省,故譯為省份不太合適,應當理解為國家或地區。意為大,亦可表示偉大,因此,可理解為大的、偉大的、神圣的國家或地區。
現存漢文史料對大理一詞的確切含義并無記載,就連生活在南宋時期并一度在廣西、四川做官的范成大對大理一詞的來源及含義也“未詳所始”。拉施特雖提到將哈剌章、大理解釋為大國的說法源于漢人,但并未詳細說明該解釋背后的緣由。盡管目前尚無法判斷“大國”是不是“大理”一詞的本意,但《史集》中給出的解釋仍可以反映出生活在13世紀的北方漢人對大理國國號的理解。當時蒙古大汗的身邊亦有不少漢人,因此這些漢人對大理國號的認識便會影響到蒙古人用蒙語對大理國的命名。關于“大國”這一解釋的由來,筆者推測,其極有可能與大理城的另一個名稱“紫城”或是大理國皇帝的梵語稱號“摩訶羅嵯”(Maharaja)有關。據元人郭松年《大理行記》記載,大理國皇都大理城“亦名紫城”。在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紫”蘊含神圣、崇高、偉大之意,常用于指皇帝的居所,如明清時期的皇宮——紫禁城。考慮到華夏文明對大理國長期且深遠的影響,因此紫城的含義應源于中原傳統文化。這樣一來,便能與《史集》對哈剌章的解釋遙相呼應。此外,受南詔、大理國時期形成的漢、梵雙重文化格局影響,大理國最高統治者具有漢、梵兩套名號。大理國《張勝溫畫卷》中多次使用摩訶羅嵯稱呼大理國皇帝,可見該名在蒙古入侵前就已存在。在梵語中,摩訶羅嵯(Maharaja)本意為“大王”,亦可引申為大的王國。《大唐西域記》中所記之“摩訶剌侘”,即今日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意為大國,與摩訶羅嵯為同一詞。蒙古人在征討大理國期間,應當獲知了大理國王的梵文名號。《元史 ·信苴日傳》記載,1256年大理國末代皇帝段興智覲見蒙哥汗時,蒙哥僅是沿用舊例,將“摩訶羅嵯”這一名號重新賜予段興智,并讓他協助蒙古官員統治云南。既然蒙哥汗可以把段興智稱為大王,那么在蒙古語中用含有大國之意的哈剌章來命名此前大理國統轄地區也是理所當然的。
拉施特獲悉大理國號及其解釋,應當來自元朝而非印度。首先,大理是一個漢式詞匯,理應來自漢地;其次,包括印度在內的東南亞、南亞印度化國家歷史上對云南的稱呼主要使用諸如犍陀羅等與佛教相關的梵文詞匯,一般不會采用大理這類漢語名稱。從《史集》記載的可靠性方面看,拉施特編寫《史集》時,不但參考了包括《金冊》(Altan-debter)在內的大量來自元朝方面的材料,還咨詢了伊利汗國宮廷中的中國學者和貴人。忽必烈派往伊利汗國的孛羅丞相深諳蒙古歷史,對《史集》的編纂也發揮了巨大作用。此外,拉施特本人也反復強調,運用每一個國家自身的書籍去撰寫各自國家的歷史是其編寫《史集》的一個基本原則。因此拉施特將哈剌章解釋為大國的說法應當是有根據的。考慮到《史集》的成書年代早于《經世大典》,基于歷史研究對史料取舍的基本原則,在缺乏有力反證的前提下,《史集》對哈剌章解釋的可靠性要優于《經世大典》。將哈剌章解釋為大國,不但符合哈剌章在元代各類文獻中指代的與大理相關的區域,在語言學方面也能得到合理解釋。“哈剌”(qara)在蒙古語中本義為黑色,但除此之外,還有多個引申義,包括大的、偉大的、神圣的等。楊富學指出,在古代突厥、蒙古語中,普遍有崇尚“哈剌”的習慣,即把一些大山、大河以及地名、國號冠以“哈剌”一詞。如:哈剌昆侖山、哈剌沐漣河、哈剌火州、哈剌契丹、哈剌和林等。這些“哈剌”如果都解釋為黑色,就說不通了。因此在理解這些名詞時,需要考慮哈剌一詞的引申義。英國突厥語學家克勞森(G.Clauson)認為,蒙古語中的“哈剌”,應來源于突厥語。中古突厥語中,哈剌亦可表示“大”。魏良張在研究喀剌汗王朝的國號時,認為傳統史書將之譯為“黑汗王朝”的做法并不合適,這里的“喀剌”應譯為“大的、偉大的”,即“大汗王朝”。因此,哈剌章中的“哈剌”,在蒙元時期亦可理解為“大”。
關于“章”的解釋,除伯希和與馮承鈞外,還存在以下幾種觀點:美國學者勞費爾(Berthold Laufer)認為“章”源于藏語jang,吐蕃常用其指代包括麗江在內的云南西北部地區;方國瑜則根據《華夷譯語》,認為“章”是蒙古語“合扎兒”一詞詞首輔音q弱化所致,意思也是地區;方齡貴認為“章”與“札忽兒歹”中的“札”為同一詞,意為漢人;然而《元史》中亦有指代云南行省下轄的羅羅斯宣慰司地區(今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的“羅羅章”一詞。根據李京《云南志略》的記載,在元代“羅羅”即指烏蠻,若將“章”理解為漢人,那么“羅羅章”就無法解釋。考慮到哈剌章、察罕章、羅羅章均為政區名詞,因此從“章”使用的具體語境看,只能將其理解為“地區”。且在對音準確度方面,勞費爾的解釋明顯占優勢,故筆者傾向于贊同勞費爾的觀點。但這里仍遺留下一個問題,那就是用于稱呼南詔的藏語詞jang的詞源究竟是什么,是藏語中原有的詞匯還是外來借詞?勞費爾曾推測,jang可能源于藏語中表示綠色的詞ljang。從藏語的發音來看,二者無疑是最接近的,但為何吐蕃會用綠色一詞稱呼南詔,勞費爾并未給出解釋。筆者認為,假如勞費爾的分析是準確的,那么這很有可能與茶葉有關。在藏語中,ja意為茶葉,讀音與jang有一定的接近度,麗江出產的納西茶亦被稱為ljang-ja。據《蠻書》記載,南詔銀生城周邊地區(今云南景東、普洱一帶)即產茶,吐蕃和南詔間的貿易也很頻繁。考慮到吐蕃與南詔間存在茶葉貿易,因此吐蕃很有可能因南詔盛產茶葉,進而稱南詔為綠色的地區。但到目前為止,勞費爾的觀點還停留在語言學推測層面,尚無法證明。除此之外,根據諸種藏文文獻的記載,jang與“詔”之間也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不排除jang是一個外來借詞,源于“詔”這種可能。在南詔語境下,“詔”本意為“王”,也可引申為“王國、地區”。“六詔”常被用于稱呼洱海周邊六個部落統治的地區。據相關學者研究,在古代藏文文獻中,jang的使用范圍在不同時期存在差異,唐代主要指南詔國,唐亡以后至明朝末年間成書的多部藏文文獻,如《紅史》《漢藏史集》等,均用jang表示南詔;明清之際成書的《薩迦世系史》《西藏王臣記》則將jang用于指代蒙元時期云南王忽哥赤統轄的區域;清代中期以后,jang的范圍逐漸縮小,主要用于表示麗江府(jang-sadam)及當地的納西族(jang-po)。可見,至少在元代以前, jang表示的地域范圍與南詔完全等同。在敦煌藏文文書中,南詔國即寫為jang,其單獨使用時,便包含了“地區”之意。此外,南詔也可寫為jang-yul,yul意為國家、地區;南詔王則稱為jang-gi-rgyal-po,其中gi為格助詞,rgyal-po即“杰布”,表示國王。因此從使用對象上看,jang和“詔”均能一一對應。在《廣韻》《集韻》《正韻》等韻書中,“詔”的讀音為“之少切”“之笑切”,和jang相比,元音部分雖存在一些差異,但考慮到二者在藏文文獻中極高的對應性,故這一假說暫時保留。此外,南詔、大理國時期用于表示地區的多個詞匯,如“睒”(失冉切)、“瞼”(居奄切)等,讀音亦接近于jang,其與“章”是否有關,亦有待進一步研究。雖然學界目前對“章”的詞源尚未有定論,但大多傾向于認為其源于藏語,并把jang理解為“地區”。蒙古人征討大理國,吐蕃是其必經之地,因此蒙古征服者將藏人對云南的稱呼納入自身話語亦在情理之中。總之,將哈剌章釋為大國或大的地區,從語言學角度看是成立的,也能與哈剌章指代的區域相吻合。蒙古統治者用大國這樣一個含有尊崇意味的表達去稱呼大理國,既能與蒙元政權對大理國統治階層給予的種種優待政策相吻合,亦是大理段氏在蒙元統治下的云南享有崇高地位的真實寫照。
《史集》在介紹云南族群時,常把當地居民依照膚色分為黑、白兩類。那么哈剌章是否與大理地區人群的膚色存在關聯?英國學者玉兒(Henry Yule)認為,《史集》中的黑色族群與服飾有關,云南地區的主要族群是撣人,撣人通常穿黑色服飾,因此蒙古人將其稱為哈剌章。這里需要明確,撣人與南詔、大理國的主體族群無關,將撣人(泰人)和云南相聯系的觀點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以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為代表的部分西方學者建構出來的,沒有任何史料依據,這已是學界共識,無需多言。據上文所述,元代對烏、白蠻的區分標準是文化而非膚色或服飾。從實際情況看,云南各族群膚色并不存在明顯差別,但李京在《云南志略》中談到羅羅人的文化特征時,指出羅羅人“手面經年不洗”,這或許是導致烏、白蠻膚色產生微小差異的原因,即烏蠻略深、白蠻略淺。因此不排除大理國歸附初期,蒙古統治者以膚色深淺來區分烏、白蠻這種可能性。倘若蒙古人用哈剌章指膚色較深的烏蠻,那么哈剌章為何會用于稱呼以白蠻(白人)為主體的大理城、大理國,卻未用于指稱任何一個烏蠻聚居的地區?大理國統治階層和主體族群均為白蠻(元代稱白人),關于大理國白人的膚色和服飾,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著名畫作《張勝溫畫卷》就提供了直接證據。《張勝溫畫卷》又名《大理國梵像卷》,據卷尾釋妙光跋文,可知該畫由大理國畫師張勝溫于盛德五年(1180)創作。畫中描繪了大理國宮廷中各類人物的樣貌及穿著服飾。這些人物的膚色絕非黑色或深色,服飾也各式各樣,與中原漢人無明顯區別。蒙古進攻大理國發生在13世紀中期,比《張勝溫畫卷》的完成時間僅晚了半個多世紀,蒙古人看到的大理國白人在膚色、服飾方面與《張勝溫畫卷》中的人物不會有太大差別,因此蒙古人也絕不可能憑膚色或是服飾將大理地區的族群視為烏蠻。總的來看,《史集》以膚色區分烏、白蠻的記載,確有一定根據,但并不意味著烏蠻和哈剌章存在對應關系。
四、“察罕章”與“麗江”
蒙元時期的云南蒙古語地名,除哈剌章外,還有用于指代麗江地區的“察罕章”,直譯為“白色的地區”。盡管與察罕章相關的材料遠少于哈剌章,但考慮到察罕章在元代史料中往往和哈剌章并列出現,因此對察罕章含義進行初步探討和推測也是有必要的。關于察罕章含義的直接記載,僅見于《經世大典》和《元史》兩種文獻,《經世大典敘錄·征伐》將其解釋為白蠻,《元史·兀良合臺傳》亦沿用之。然而,這與《經世大典》和《元史》對哈剌章的解釋存在同樣的問題,即白蠻這一解釋無法和元代麗江地區的主體族群相吻合。若對蒙元時期麗江地區族群構成及蒙古人對當地的命名特點進行分析,那么將察罕章釋為白蠻的觀點就難以自圓其說。據《元一統志·麗江路軍民宣撫司》條記載,麗江“蠻有八種,曰磨些、曰白、曰羅落······參錯而居······磨些蠻最多于諸種”。在《蠻書》和《云南志略》中,均將磨些蠻歸為烏蠻一類。可見,在元人眼中,白蠻與磨些蠻是兩類完全不同的族群,認為蒙古人視磨些蠻為白蠻的觀點顯然與史實相悖。也許有學者會將《元史·世祖紀》元憲宗三年十一月“師次白蠻打郭寨”一語,作為“磨些蠻=白蠻”的依據。然而,上文業已提到,麗江地區的族群,除磨些蠻外,亦有白蠻,二者參錯而居。因此,《元史·世祖紀》中打郭寨的白蠻,與磨些蠻并非同一族群。
《元一統志》中的記載亦揭示出,被歸為烏蠻一類的磨些蠻則是當地人數最多的主體族群。在蒙古征討大理國期間,最先歸附蒙古并在此后一度擔任麗江地區最高軍政長官——察罕章管民官的麥良家族就屬磨些蠻。既然元人將磨些蠻歸為烏蠻類族群,那么如果依照磨些蠻的族群稱號來命名該地,便不會使用表示白色的“察罕”一詞。此外,在元代文獻中,察罕章指代的地域范圍十分明確,僅限于麗江一地,而白蠻在西南地區則廣泛分布。因此,從該詞的使用情況看,白蠻的解釋也是站不住腳的。除此之外,或許還存在一種可能,即察罕章是否會源于《元史·世祖紀》中的打郭寨白蠻呢?筆者認為,如此解釋看似雖有一定道理,但目前仍缺乏直接相關的史料依據。更主要的疑點是,倘若察罕章的命名依據是族稱,那這就很難解釋蒙古人為何會將白人居住的大理城稱為哈剌章,因為上文業已論證,元人自始至終從未將大理白人視為烏蠻。更何況察罕章宣慰司的治所在當時麗江巨津州半空和寨,此寨地勢險要,是典型的磨些蠻聚居區,因此可將這里看作察罕章最狹義的范圍。假如蒙古人用察罕章稱呼麗江地區的白蠻,這便無法解釋該宣慰司的中心為何會設在一個地勢險要的磨些蠻村寨。
值得注意的是,在蒙元時期的麗江,“察罕忽魯罕”是除察罕章外的另一個蒙古語地名,是蒙古人對麗江路所轄寶山州部分磨些蠻村寨的稱呼。據《華夷譯語》,溪水在蒙古文中譯為“豁羅罕”,與“忽魯罕”為同一詞,故該詞直譯為“白色的溪水”。又據《元史·地理志四》記載:“寶山州,在雪山之東,麗江西來,環帶三面。昔么些蠻居之······世祖征大理,自卞頭濟江,由羅邦至羅寺,圍大匱等寨,其酋內附,名其寨曰察罕忽魯罕”。可見,對于歸附的磨些蠻村寨,蒙古征服者并未使用與磨些蠻或烏蠻相關的族群稱號,而是根據江水等與白色相關的自然地理事物來命名。至元十五年(1278),元朝將察罕章宣慰司改名為麗江路,“路因江為名”。“麗江”指金沙江,“麗江路”這一名稱也和江水有關,察罕章和麗江亦存在替代關系。因此,從蒙古人對麗江部分區域的命名習慣和特點來看,察罕章中的“察罕”,很有可能與“察罕忽魯罕”中的“察罕”一樣,也是用于修飾江水、雪山等具有白色意象的自然地理事物,察罕章的含義極有可能與之相關。雖然上述對察罕章一詞來源的討論仍主要停留在推測層面,但有一點是可以明確的,便是就目前已有的材料來看,察罕章與麗江境內的主體族群磨些蠻以及當地人群的族稱并無直接關聯。
五、結語
綜上所述,哈剌章在蒙元時期一直用于指代大理城、大理國等與“大理”相關的地域概念,察罕章的使用范圍則僅限于麗江一地。在廣義語境下,哈剌章的范圍可包含察罕章。然而,大理、麗江地區的主體族群分別是白人和烏蠻類中的磨些蠻,烏蠻和白蠻之間亦不存在包含關系,故哈剌章、察罕章與烏蠻、白蠻無論在分布區域還是相互關系上均無法對應。一般認為,在蒙元帝國早期,蒙古統治者缺乏華夷觀念,通常不會將被征服地區的人群視為蠻夷。因此從蒙古人的命名習慣上看,哈剌章、察罕章與烏蠻、白蠻也難以等同。哈剌章的確切含義,應當是14世紀初期伊利汗國宰相拉施特編撰之《史集》中的解釋:“大國”,亦可理解為“大的地區”。根據《張勝溫畫卷》所描繪的大理國宮廷人物的膚色和服飾,可知《史集》所記云南地區黑膚色人群,與哈剌章并無關系。雖然將哈剌章、大理國解釋為“大國”的說法僅見于《史集》,但綜合現有各類材料來看,這是迄今為止最為合理的解釋。根據蒙元時期麗江地區的族群構成及當地蒙古語地名的命名特點,指代麗江的“察罕章”,其含義極有可能與江水、雪山等具有白色意象的自然地理事物相關。《經世大典》的編纂者在不了解哈剌章、察罕章原始含義及指代區域的前提下,僅憑“哈剌”“察罕”在蒙古語中分別意為“黑色”“白色”,便將哈剌章、察罕章與烏蠻、白蠻隨意比附。這一錯誤解釋亦被《元史》編撰者吸納并沿用至今。明確了哈剌章、察罕章與烏、白蠻之間的無關性,亦有助于進一步厘清和明確蒙元時期云南地區相關族群概念的具體內含。
在現存的多種元代文獻中,很容易看到這樣一種現象,即蒙古人征服一片區域后,時常會用蒙古語或突厥語詞匯來對當地的城鎮進行命名。例如著名的黑水城在蒙古語中稱為“哈拉浩特”(Qara-qoto),意為“黑城”;《史集》所記河北真定府被蒙古人稱為“察罕———八剌合孫”(Caqan-balaqasun),意為“白城”;《馬可波羅行紀》將四川利州記為“阿黑八里”(Aq-balīq),也意為“白城”。顯然,這里的黑城、白城與當地居民的族群身份并無任何關聯。這提示了我們,在研究哈剌章、察罕章的詞義時,不應被《經世大典》和《元史·兀良合臺傳》的權威性記載所限制住,而要用批判的思維,從多個角度審視其所記內容是否合理。
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曾說,“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這句話雖是立足于古漢語訓詁學而言,但卻揭示出歷史名詞背后蘊含的文化史意義。“哈剌章”“察罕章”雖是蒙元時期出現的云南政區名詞,但其中蘊藏的歷史文化信息亦不容忽視。從構詞角度看,二者均由蒙古語和藏語詞匯共同構成,體現了藏文化在蒙古征服者認識云南過程中所起的媒介作用。此外,云南自南詔大理國以來形成的漢、梵并存的雙重文化格局對13世紀蒙古人認識云南亦產生了重要影響,“哈剌章”的漢譯“大國”與大理城及大理國皇帝梵文名號“摩訶羅嵯”間存在的密切聯系便是例證。總之,哈剌章、察罕章含義的背后,暗藏著一幅蒙元時期云南地區漢、梵、蒙、藏多種文化相互并存、碰撞、交融的生動圖景。
作者:李心宇
來源:《學術探索》2021年第9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宋柄燃
校對:劉 言
審訂:李春燕
責編:耿 曈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歡迎來稿!歡迎交流!
轉載請注明來源:“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眾號
- 熱門文章
- 最近發表
- 隨機文章
- 標簽列表
-
- 最新留言
-